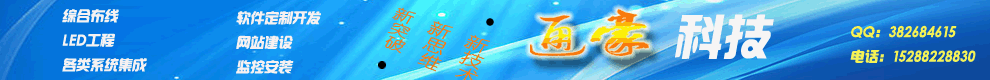我想这相似于一次集体拜年,只不过是以歌舞的形式。令人感叹的是这种形式充满了人情味,村庄在一派歌舞升平中既欢度新年,又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曾经有过矛盾的人家,此刻互相走到一起,同唱一支歌,合跳一曲舞,还有什么恩怨在这浓浓的乡情中不能化解的呢?

我想起了我们的新年,噢,在藏区我总是把所见到的和我们汉族人所经历的相比较,这就是文化的差异使然吧。新年里我们到朋友亲戚家串门,也只能说几句“拜年了”之类毫无特色的话,然后给小孩子们散发压岁钱,对孩子们来说那是过年最让他们激动的事情。或者,在这个信息化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把传统的拜年简化得更彻底,打个电话,在手机上发条短信,或从网上道一声“春节快乐”,我们便觉得该尽的情义完成了。我们要恭贺的对象连我们的面都见不到、甚至连我们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们可否在新年里为主人唱一支歌,跳一曲舞?我们可否在新年的第一天,一大早起来就怀揣着一份美好的期盼,把火塘烧得旺旺的,准备好最醇香的美酒,恭候一村庄的朋友来家里做客?不,我们汉族人不擅长这个,我们也没有候客的火塘,或许我们早就忘了这些最人情化的东西。我们的热闹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会驾车出门旅行,会和朋友一起“砌长城”,会找个地方去轻松休闲等等。可是它有多少文化和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呢?我们能找到多少过年团圆的滋味,找到那份一年中朋友亲戚之间难得的温情呢?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每到春节,城里的人们宁愿千里迢迢跑到乡下去过年的缘故之一吧。
那天我曾经诚恳地邀请七林培楚当场为我们表演一段情舞,我想见识一下这位情舞“老王子”的风采。但是遭到了七林培楚的婉拒,他总是扯三道四,就是不肯站到屋子中央一展舞技。我那时怀疑他是否老了,再也跳不出像风一样流畅自如的情舞了。从他家出来后吹批才告诉我说:“大哥你真会难为人家,培楚怎么可以在家里当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妇跳情舞?我们藏族人跳情舞非常讲究辈分和长幼,同辈的人才邀请对方跳,不同辈的人是绝不可以跳情舞的。”
我感到有些害臊,我把情舞理解得太庸俗了。后来我才知道,虽然说是情舞,但是绝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随便。情舞分为三大类,分别叫做“擦沾”、“擦中”和“擦喜”,前两类是在婚嫁时跳的,我在村庄里参加的那次婚礼上,人们开初跳的就是“擦沾”和“擦中”,这种情舞男女老少都可参加,歌词内容多为祝福、恭喜之类的吉祥话语;“擦喜”则是年轻男女谈情说爱时跳的舞蹈,或者按我们的理解,是真正的有情而跳、有感而唱的爱情之舞。
吹批还告诉我说,藏族人其实是很内向、传统的,年轻人跳“擦喜”情舞时,人们要先唱一首歌《叶勒循儒》,意为请老人家和小孩进家去,我们年轻人要在一起跳情舞了。甚至连同一个村庄的人都不能在一起跳情舞,因为村里到处都是自己的表姊表妹、叔伯兄长,情舞更不能当着自己的长辈跳,情舞的调子年轻人在家里连哼都不能哼。因此在人们唱起《叶勒循儒》时,老人们都知趣地回避了。
到这时我才弄明白,尼西的情舞比我想象的要严肃规矩得多,甚至到了刻板的地步,人们要跳情舞一般都是到外村去邀约伙伴跳。大年初七,汤满的各个村庄的年轻人会聚集在一个叫“臭水”的地方互相跳舞。那是几个村庄的年轻人新年里第一次聚会,那时真正的情舞才开场,许多年轻人在这个情舞聚会里将会找到自己的意中人,也有一些情舞高手,将在这一天里奠定自己情舞王子的地位。(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