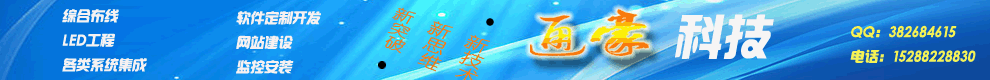舞者丽萍,现在确实在往精灵和神的路子上飞奔,就没人想明白,单是外貌,现在的她和十几年前的她怎么就没有任何区别?十几年前,虽然高兴得过了头,但还敢和他站在一起合影并高调晒出来,十几年后,虽然还有合影但实在不敢晒出来了,丽萍还在貌美如花而我们已变成光头大叔,不能自毁形象。去年曾邀她去维西哈达,看她一头青丝,想起自己满头白发,便随意问她是否染了发?人家说没有,天然的。害得我当场就想质问苍天大地的超级不公。
杨姐丽萍,这些年一直努力稳稳的走,本就是天才但绝不辜负天才,光鲜的背后绝对是一颗强大的心。这几天丽萍及她的团队在台湾,听说宝岛风大,被她们遇上了。有一日见她助手陈玲发微信说瞧她跳舞想流眼泪,仔细一看才知道因台风影响,为不让买了票的观众失望,要在天气较好一天集中连演三场孔雀,肯定有人建议了可以取消一场,毕竟台风是不可抗力,助手想哭一定是因为感动与心疼。但我想她强大的心肯定不会听,当年在雪山较劲,现在也不会向台风认输。何况乎她清楚要怎么对待喜爱她的人群。
舞台下她通常依旧是邻家大姐,对所有事,能展现满满慈悲。甚至于在红遍天下忙不过来时,还会抽空打来电话,只为邀请几个曾经陪她去采风的朋友去参加她新节目的首演仪式。听说有人问她原因,她说因为他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后来我想,她的几乎无可挑剔的全面成功,与香格里拉梅里雪山的眷顾是有关系的。2000年春,雪还封山,在她的坚持下,我们在雪地里推车过了白茫雪山。因此我相信,她应该是全世界在新千年,第一个朝拜了梅里雪山的明星舞者。
今天,就发一下记录杨丽萍在香格里拉的文章。

杨 丽 萍 在 香 格 里 拉 (上)
生活教会我们的生存方式大概是:吃饭、喝酒、睡觉、阅世以及和朋友聊天,因为现代社会已经很发达的缘故,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地接受着各种有用或无用的信息,程序化的工作有时也就会脱离原有轨道几天。偶然的机会,朋友从远方来电话,杨丽萍要来迪庆采风,希望能接待好,当然是毫不迟疑地应承,一段行程的开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知道杨丽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能看到的舞蹈不多,便疑心《雀之灵》是来自天外的舞蹈,静静地在电视前欣赏完舞蹈后,就记住了一个美丽女人的名字及一双让人难以释怀的手。
许多年的日子总是平平常常的滑过,后来还是在电视里,又看到了她的舞蹈《雨丝》、《两棵树》等等,依旧是那双手,演绎着一种痛苦和追求,从而成就起一份在心里的完美。和绝大多数的观众一样,我并不懂舞蹈,看不出表演过程中也许是很复杂的一些舞蹈语汇,但深切地感觉到了表演画面和意境的美,没有什么理由,你不由自主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及这一双手。

杨丽萍在迪庆采风的时间不长,仅有五天,到了梅里雪山、奔子栏、属都湖,很多精彩而也许相对精致的地方反倒是没去。但因为一种相处的真实,所以有机会处在一个较近的位置,如照相般,记录下平常难以感受到的生活片段。
迪庆之行,更多的时间是同处一车的旅途,其最大好处就在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得去交谈,而通过交谈,人与人总是要走得近一些。

相处的几日,感受最深的是一份随和,没见到她的大喜,也不可能更多感觉到她的内心,她举手投足之中透着一种大家风范,很多场景所表现的大气和恰如其分对度的把握,真正显现出了艺术大家的气度和风采。艺术家行列之中,她显然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她的地位是由她独有的舞蹈语言形成的。曾经记得这样一篇报道,美国著名的实业家哈默博士,在其艺术博物馆落成之日,大宴全球10名艺术大家、全亚洲唯一受邀的只有她。也许,哈默博士的邀请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甚至于哈默原来大概也只算是一个投机者或附弄风雅者。但不管怎么说,舞蹈界的尊者地位,她倒是担当得起了。我还曾思忖过一个问题,千千万万的舞蹈者,肯定会有成百上千的舞蹈者在各方面的条件超越她,何以这么多年来大成者总是寥寥无几?而且她似乎并不属于作品高产者,至少到今天为止,我实在不知道她还有多少优秀的舞蹈作品?然而,她却以一种无与伦比的王者之气成功地存活在舞之殿堂的顶峰,以巨大的影响力把一种魔幻般的印象根植在普通观众的脑海里,究竟是为什么?我想,我似乎从她的随和中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属都湖畔的草地上,她在一个牵着马的藏族汉子身旁如蝶般欢快起舞;在梅里雪山脚下的茶馆里,她和布满皱纹的藏族老阿妈愉快的唠叨拉家常;在奔子栏排练舞蹈场地,烈日下她仔细地观看着舞蹈队的一招一式。然后随时随地给崇拜者签名、跟他们合影。她并非乐此不疲,但只要可能,她便尽可能的满足。我曾问她:“太多的人与你合影,你如道具一般,是否感觉到很无奈?”她回答:“无奈也是一种选择啊!既然选择了这条路,这种无奈是最起码要承受的!”很平常地回答,使我缄默。随和之中透发而出的深厚功力,逼人尊敬。

一种敬业的精神是足以感动人的。白马雪山上,要拍照,她便只穿一件单衣,按摄影师的要求,躺在雪地里,四月的雪是潮湿的,很快就会湿透衣服进而十分寒冷,而她竟可以长时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同样也是在白马雪山,因前面有车陷在雪地里阻了路,天已晚,很多车纷纷掉头回返,同行的人在前进与回返中也有了大的争议。当她听说德钦会有一些原汁的舞蹈录像素材后,长时间没吱一声,同行的人便知晓了她继续前行的决心。晚上十点的时候,路通了,在冰冷的夜里,过了白马雪山。看藏族婚礼歌舞的录像资料时,因听不懂藏语,对长时间慢节奏的歌舞对答一无所知,我便在慢节奏中昏昏欲睡,她肯定也是听不懂在唱些什么,但她却看了一盘又一盘,真是佩服她。

品茶闲聊的时候,她讲起在大理洱源老家的童年,打柴遇狼的场景在我们成年男人的童年都已是一些遥远而生疏的回忆了,甚至于没有,但她却很真切地讲起了这种场景。她很平常地讲起孩提时在村子里篮球场自发组织跳舞的童趣,很坦然地说起孩提时用六六粉去杀死头发里虱子的真实。
我暗地里想,这么多年来,绝大多数的名人,尤其是女名人肯定不会有类似的回忆和如此讲述自己的童年。很多人的脑袋里仅残存着一种意识:高贵是与生俱来的,诉说起自己平常的往事或许就会与身份不太吻合。于是,名人大多数变成了非人。遇到杨丽萍,使得自己重新理解了名人真实的可贵。因为她是名人,她便逃不脱名目繁多的宴请,席间她通常并不多言,她很善于并乐于倾听,尽管她通常要处在中心位置,但她不太多说,便没有给人留下太多张扬的感觉。偶尔她会给谈话者一两句理解的附和,谈话者便情绪更高,而她则能够继续倾听。

她是兼收并蓄之人,阅世的目光非常清澈,无疑已拥有自然行于世间的练达,金庸先生所描绘从剑、重剑、木剑到无剑的剑客境界,提供了一份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当一个两手空空、平常随和的人来到你身边时,一种由心灵所能感受的大的场也就在这个范围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