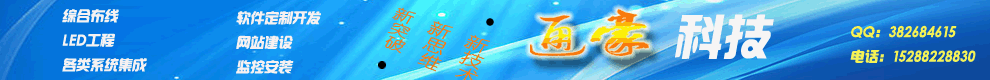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发,往西北方向开车一个半小时,道路越来越窄,道边白杨树的沙沙声越来越响,这时你会赫然看见一块指示牌,“小毛驴市民农园”到了。
春末的北京已经有些炎热,远处的凤凰岭清晰可见,农场的空气十分好,时不时还有四声杜鹃悦耳的鸣叫。顺着引水渠边的道路,我们走进“小毛驴”,两侧的一排排菜苗长势喜人,玉米、包菜、甘蓝、西葫芦、西红柿在一片片被精心划分为小块的土地上各自为阵。有些小块的土地上还立着诸如“寻梦园”这样的牌子,它们的主人几乎每周都会从几十公里外的北京市区赶到这里,给土地松松土、浇浇水,顺便采摘一些成熟的蔬菜回城。
“小毛驴”种的几乎都是应季的蔬菜,创办人石嫣管这叫“种在当地,吃在当季”。他们现在开放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配送份额”,农民来种,会员每周会收到农场配送的有机蔬菜;另一种是“劳动份额”,会员需要每周到农场参加劳动,“小毛驴”以30 平米为单位划分了土地租给会员,自己种自己收。“小毛驴”提供种子、有机肥料、水、技术指导。加入的会员预付一年的“菜钱”,前者要比后者贵一些。
这种农业生产模式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最早源于瑞士和日本。农民在每个种植季节之初,就与消费者签订一份购买协议,消费者把本年度购买农产品的钱先期支付给农民,农民则承诺不使用化肥和喷洒农药。这种方式绕过了中间商,让农民直接和消费者面对面,于是,农民能收获到较多收益,消费者吃上了生态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土地也因为没用化肥而蓄养了地力。
这种模式,是现行工业食品制造体系下的另类选择。石嫣觉得,在食品安全备受威胁的今天,是时候让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重建信任了。
自然耕作的试验田
端午节刚过,农场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两只上年纪的大黄狗带着“儿女们”四处乱窜。戴着宽檐农民草帽的石嫣熟练地踩着田边的细埂给我们引路。黄瓜开始爬架子开花了,生菜一茬茬地冒出来,心里美小萝卜基本上可以吃了。石嫣对这里的每一种蔬菜都了如指掌。“今年干旱,蚜虫特别多,你看这棵西葫芦,因为有了蚜虫,就好像封住生长点那样,没能长起来。”她指着路边沟里一棵耷拉着脑袋的菜苗说,边上的明显比它高出一截。那棵菜叶表面布满了白色点状物,石嫣说,那就是蚜虫,有些是卵,有些已经成虫。“有蚜虫的地方蚂蚁也多,蚂蚁喜欢舔蚜虫屁股上的甜浆液吃,蚜虫没有蚂蚁舔屁股,就难以活下去。”果不其然,菜叶的阴影下,十来只蚂蚁匆忙地来来去去。
“每一件事都在影响着另一件事”,这些微妙的食物链知识是石嫣接触土地后才慢慢积累起来的。石嫣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农学博士。她从本科学农一直读到博士,却一直不了解农作物是怎么种出来的,直到她去了美国。在她读博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美国农业政策与贸易研究所(IATP)的邀请,去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劳动半年。 IATP 是美国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旨在运动实现公平、可持续的食品、农业和贸易体系。她去的就是一个家庭经营的CSA 模式农场,在那里,她像一个美国农民那样学习如何育苗、除草、浇水、移植、耕地,CSA 农场要保证农产品绝对不能施加农药化肥,也不能使用能耗大的机械。农场只有一台小型拖拉机,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人工完成,劳动强度超出预料,在疲惫的一天天劳作中,她逐渐了解了土地,也越来越亲近土地。
从美国回来后,她就将美国的模式搬到了北京。“小毛驴”这块地原本属于沙涧西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有机农业示范教育基地。石嫣的导师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拨给”她20 亩地做“CSA”的实验,结果从2008 年一路做来,规模越来越大,做实验的土地从20 亩扩大到230 亩,客户也从最初的54 户增长到600 多户。
“农民是非常有智慧的,打个比方,以前的农民会观天象,看小动物的行为,用一些聪明的方法治虫害。现代人变得弱智了,看到虫子就想到农药,东西长得不好就想到化肥。”石嫣对我们说。
今年蚜虫泛滥,坚持不用任何农药的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比如在土上撒草木灰、倒烟叶秆子水,辣椒水也用过,“效果不是非常好,有时候帮我们种地的农民都替我们着急。在农民看来,蚜虫只要用很微量的农药就可以除掉。”有时候,也会有消灭不了的敌人,比如去年蒿子秆发生了严重的斑潜蝇灾害,这种虫子只有用剧毒农药才能除去,“小毛驴”的配送份额会员在当季便没有收到蒿子秆,种蒿子秆的劳动份额也颗粒无收。他们只能将得病的蒿子秆深埋,沤肥。“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及时通知会员,来这里看的消费者也会了解实际情况,社区支持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种植者和消费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石嫣说。
时值工作日,农场里没有参加劳动份额的市民在劳作。一片30 平米的小菜园搭配得当,每周能为一个家庭提供10 多斤新鲜蔬菜。小田的耕作方式和大田完全不一样。石嫣说:“大田种菜到时间会把弱苗除去,让壮苗好好长。小田里就不一样,市民会先把长大了的摘回去吃,留小苗慢慢长。”旁边正在配送份额地上摘莴笋的农妇忍不住抱怨:“种小田比以前种大田累多了。以前只要一播种、一施肥就完了,等收,有虫就打药,现在种地像绣花。而且种完了一种菜又是另外一种菜,没得歇。”
她们是“小毛驴”团队雇佣的当地农民,“小毛驴”所在的沙涧西村已经名存实亡,农民通过市政拆迁住进了楼房,拿着几百万的补偿款,被石嫣他们“返聘”回去种地,一个月挣1000 多元工资。
石嫣站在农妇旁边笑笑,这样的抱怨她经常听到。田埂边上不时能看到一口大缸,上空苍蝇乱飞。“那里面是我们自己做的麻渣酱肥。”石嫣告诉我们,“主要是轧过油的芝麻渣放水沤出来的”。除了种菜,农场还在原先遗留的苗圃上,用铁丝网围起了两亩地,散养几百只鸡,鸡吃虫,除草,鸡粪又变成了有机肥料。菜地边缘的一排小房子里,是他们养的几十头猪。小毛驴农场在猪栏底部铺上添加了微生物菌的秸秆、木屑、米糠,用这些垫料吸收粪便,不需要化学消毒剂对猪栏消毒冲洗,在使用一年半后垫料也可以当作上好的有机肥料。猪圈旁边的小房子里,摆满了坛坛罐罐,都是石嫣他们自己制作的各种有机肥。“磷酸钙”是用鸡蛋壳做的,“天惠绿汁”的原料是生长中植物的茎叶。
但无论蚯蚓粪、麻酱渣,还是其他有机肥料,和化肥和生长素比起来,有机肥的效用要慢得多。石嫣说,刚开始的第一年,由于土壤的肥力不够,种出的空心菜、西红柿、小白菜等蔬菜,跟超市里的比起来,的确个头不大,卖相不佳。但经过两年的耕种,地力在逐步恢复,长出来的菜也越来越好。她的博士同学程存旺通过在苏州做大田实验,认为刚开始采用有机方式种植的农作物产量也许会有下降,但只要坚持3 年,等地力恢复后,产量就可以接近用化肥种植的水平了。
消费者也逐步接受了这样的差异,一位“小毛驴”的配送客户李佳佳对《外滩画报》记者说: “有些菜,看上去烂兮兮的,比如西红柿和黄瓜,但味道真的好,十分浓郁。还有一次,从菜里爬出一条大青虫来。”她也有做一个农场的打算,“现在,三聚氰胺,各种添加剂和各种农药生长素太多了,很难想象我的孩子将来要吃这些食物长大。我们小时候吃苹果,水洗洗直接可以吃了,一口咬下去,脆生生的,酸甜酸甜的,透着一股清香。工业化大生产,各种化学品的使用,那些精微的体验,统统都没有了。”
城市新农夫运动
石嫣即将出版的一本翻译著作叫《四千年农民》,是一百年前一位名叫富兰克林•金(Franklin King)的美国农业土壤局局长访问中国、日本和朝鲜后所写。他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解答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农夫种了几千年的地,土地还是照样肥沃。答案是中国农夫懂得精耕细作,以粪为肥。
石嫣的导师温铁军认为,中国过去五十多年的大机械化、规模化、化肥化农业发展模式并不成功,唯一实现的化肥化,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他现在相信,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业,回归生态化势在必行。
所以当导师给地让石嫣做生态农业的试验时,她还觉得挺开心的,总算可以过上梦想中的农夫生活了,“无论外界纷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然而,“小毛驴” 真正运营起来,她觉得离自己的田园想象还是挺有距离的,这个农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做。常常有人讨教她做农场的经验,她都劝别人:“真想做的话还是做家庭式农场好,有另外的产业支撑着你这块地,只种一些给家人和朋友吃。”
农场的工作人员里有不少生态农业爱好者,他们在这里学习农业知识、体验自然生活,也思考着自己的农业计划。刘记虎曾经在“小毛驴”待了7 个月,从志愿者到实习生到正式员工,今年转去常州武进CSA农场工作,这是“小毛驴”在常州的拓展项目。他毕业于一所农业大学的畜牧学专业,他将原先的工作描述为“给社会投毒”,他曾在一家大型公司养鸡,“四万多只鸡苗进去,从出生开始就不停地打药,35-40 天出栏的时候还会死一万多只,药都控制不住。鸡的生活空间非常狭小,转身都困难。”他对记者说,“我原来的公司已经算不错了,对病死鸡做无害化处理,一些小公司难以想象会怎么处理。”
在这里,他学习生态养殖,自己做肥料,培养菌种,每天早睡早起,过的生活简单自然,但把工作几年的积蓄几乎都赔进去了。“做志愿者的时候是没有工资的,但包吃包住,实习生的时候给600 块的补贴,转正后,工资涨到1500。”他说。但他仍然觉得为这样的事情付出十分值得。
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农场里有很多。实习生里,有毕业后暂时找不到人生方向的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有从IBM 辞职,决定回归田园的。“小毛驴”农场成了农业发烧友们回归乡土生活的第一站,他们在这里学习农业知识、思考自己的农业计划。石嫣每每劝别人慎重辞职: “干农活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在现在的政策下,做这样的农场最好还是别做全职。”
“小毛驴”本质上还是一家企业,隶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后者是一家非盈利性社会企业,2008 年5 月成立,注册资金30 多万元人民币。注册资金由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香港中文大学刘建芝等教授捐赠而来。由最早的20 亩地发展到现在的230 亩。“我们过去是去是按照NGO 运作的,但这样农场持续面临资金问题,只有形成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才能持久,所以只能以项目方式运作。我们现在60% 的利润,都在做实习生培养。”石嫣说。
尽管是做农业,他们却没能享受农业补贴和其他减税政策。“因为农业公司要求注册地有房屋,你不能拿土地去注册,我们现在正式的办公地点在市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我们周围村子里有个村民,拿院子里2 平方米的鸡窝就注册了一个农业公司,我们就不行,因为人家是房屋的所有者。”石嫣说。
石嫣告诉我们,也有许多风投来找过“小毛驴”,但他们大都要求3 年的回报期。还有比如一个猪棚,只能放10 头猪,按风投的规划就放100 头,他们觉得这是原则问题,不能妥协,都拒绝了。
尽管困难重重,许多都市人还是身体力行地做了起来,对他们而言,务农好像是一场自然的禅修。5月末,在上海“农好农夫”市集讨论现场,十几个在全国各地做小农场的新兴农场主们交流着种地经验。一位在现场参加交流的市民在崇明认租了一小块地,她向记者描述了给西红柿蔬果的场景:“小蕃茄果距离地面也就二三十厘米,个个低着脑袋,简直是趴在地上往上看才能看清小番茄全貌,这样才能发现是否有裂果,好把它摘去。要单腿跪在地上,感觉很像练瑜伽。”
老贾原来是一位职业经理人,搞自然农耕有几年的时间了,今年在崇明岛租了近百亩土地,种水稻。台湾东吴大学的退休教授郭中一退休后在合肥西郊铭传乡搞了个“香草农庄”,种香草,也种当季蔬菜。这些都市新农夫们原先大多有固定的工作,收入体面,老贾在自己的博客文章“我为什么选择做农民”里写道:“自然农业也不一定是指农业技术,它更应该是一种人生态度,不强求、不妄为、不自欺、不欺人、诚实感恩。”
石嫣也说,其实很多食品安全事件,农民并非有意下毒,而是在原有的农业价值链中,收益得不到保障。CSA 农场不仅是农民给消费者提供好的食物,消费者也有义务帮农民增加收入。温铁军教授也赞同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壮劳力都去打工了,剩下的当然喜欢种省事田,种子一下,化肥一撒就完了。种田比打工赚得少,农民怎么会好好种地呢。
有机之辩
“自然农法”、“生态农业”是记者在和小农场主们交流时时常听到的词。谈起“有机”,却颇为尴尬。
有机农业从上世纪初开始萌芽,在美国人富兰克林•金写了《四千年农民》后,一些草根的社会运动家逐渐开始实践书中记载的有机农业做法,并倡导注重农民权利,公平贸易。事实上,有机农业就是最古老的农业形式。二战结束后,人们发现战争期间发明出来的技术对农业生产颇有帮助。例如,被作为炸药使用的化学药品硝酸铵摇身一变,作为肥料派上了用场,而被用作神经毒气的有机磷化合物后来被用作杀虫剂。农业生产方式趋向工业化和密集化。有机农业被冷落,几乎处于停滞。然而在这一阶段,生态环境破坏,生物多样性下降,病虫害抗药性增强,一些次生病虫害大量发生使发达国家开始反思,上世纪70 年代初掀起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的各种替代农业思潮,有机农业的发展开始受到重视。
1972 年,国际有机农业联盟会(IFOAM) 在法国成立;1975 年,英国成立了国际生物农业研究所;日本1971 年成立了有机农业研究会,1985 年成立了自然农法国际研究中心。有机农业的形式也趋多样化,美国把有机农业称为再生农业,英国和西欧称为生物农业,日本叫自然农业,另外还有生物动力农业、低投入农业等,他们的共同主张都是反对石油农业,反对使用化肥、农药、化学除草剂、饲料添加剂等化学产品。1976 年,美国出台了有机农业法,开始制订“有机”的标准。
“那时候商人们看中有机的商机,‘有机’开始成为一个产业,在中国,最先引进有机农业的是农业部的人,有机是作为一个产业被引进的,却忽略了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反思和继承。现在提到有机,大家的印象就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最初的保护农民权利,公平贸易等反而被人忘记了。”石嫣说。
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显示,目前全国有20 多家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规模不等、背景不一,还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机构来认证所有的有机产品。在中国,农产品分为无公害、绿色、有机三个等级,这些标准的主要区别在农药化肥使用量不同,简单说绿色食品要减少使用农药和化肥,获得无公害认证的产品不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化肥。
有机食品认证是食品质量认证的最高级别,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人工合成物质,对土壤、空气、水等环境质量都有很高的要求。
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认证都需要花费一笔不菲的费用。小农场主们,有许多尚且在“亏钱种地”,更别说花一大笔钱去做有机认证了。于是,得到认证的大多是将有机农业做出规模的大企业,商店和超市里的有机柜台摆放的大多是这些产品。“有时候,政策不得不逼迫你成为三无产品。”石嫣说。
台湾教授郭中一在小农场主的讨论会中发言:“看到有机食品展中,大公司陈列出的硕大丰美的果实蔬菜,我深深震恐。冠以有机之名,消费者便放心食用,然而真正从事有机农耕者皆知,如此品相优良的农产恐非有机耕作所能得。”大公司还是前赴后继地来了。青云创投总监左林认为,有机农业在未来几年会是一个暴发性的市场机会。
小农场主们声称大规模种植有机作物根本不现实,理由是一旦发生病虫害,根本无法控制。天然杀虫的效果比农药慢得多,等到起作用的时候菜也枯死了。方舟子则认为“零农残”几乎不可能实现。“空气中、土壤中、水中,本来就都含有种种有害的化学物质,能被作物吸收,根本不可能保证‘零农残’,只是量多量少的区别。”
石嫣认为“小毛驴”虽然没有去参加有机认证,但一年年增长的订户获得了消费者的“认证”。 “要善待土地,土地最诚实,你呵护它,它就回报你,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
她说。曾邀请石嫣去美国农场劳动的美国农业政策与贸易研究所负责人郝克明(Jim Hackness)来“小毛驴”参观时对记者说:“这里作为一群研究生的生态种植实验,是非常成功的。但她(石嫣)也十分清楚,有机种植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本文来源: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