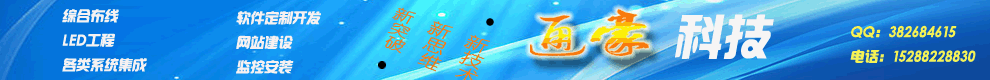四季农活中,插秧无疑是惬意并富有诗情的一种了。双脚浸在水田里,触着阴凉柔软的烂泥,不似刈麦割禾那般暑热蒸人;双手捉了碧绿的秧苗,在错落有致的田畴上作画,将刚刚枯黄过的大地又点染得绿意葱茏。
和玉米豆麦类植物的点种不同,秧苗需要移栽方能获得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更加壮硕的成长。看那一畦畦待移的秧苗,青翠欲滴的头在秧亩田里日夜翘首,多像那暂寄娘家的待嫁姑娘。盼望有一双手将她们连根拔起,于水中淘洗干净,再清清爽爽地出阁。拔秧是个细致活,必得紧抓根部,每次只抓一两棵,缓慢加力方能顺利拔出,娇嫩的秧苗很容易因蛮力的揪扯而断裂的。清凉的早晨,走进田间,拂去秧叶上浓重的露水以及被露水打湿的灰白的蛛网,搭了条凳在混合着草香味和泥腥味的秧母田坐下,熟练的庄稼人会左右开弓,“刷刷刷”,边拔边在水里涮洗,抖落掉须根上一些顽固的泥。拔到双手攥满,再用浸湿的去年的稻草将她们拦腰交叉捆绑,仿佛扎辫子一样。捆好的秧苗叫秧把子,她们被整齐地码进土箕。白嫩的须根、扁平的腰身、翠绿的叶子,每一棵秧苗都吐纳着健康有力的呼吸,浑身胀满了青春活力。负担起如此水灵的新娘,步履轻松地走在宽宽窄窄的田埂上,不时抬起眼,远望此时还是百衲衣一样的田畴,心中便有了改天换地的豪情。夏日田野,薰风拂面,令人神清气爽。
秧苗的新家是一块块刚刚平整出的水田,田埂刚刚被一把湿淋淋的水锄糊抹过,以免水从田埂渗漏。糊好的田埂还可以种黄豆,往往豆未熟而谷先黄。漫灌水田的大水来自遥远的雪山融冰,囚禁了一冬的水翻滚过不知多少条大大小小的沟渠,最终到达刚刚拾掇好的油菜田或麦田里,又一次安静下来的时候,依然裹挟着冰雪的温度。探脚进去,有些砭骨,那清凉正好抵消了脊背上的灼热。原本清澈的水流被牛拉的耙子一趟趟搅过后变得浑黄不堪。浑浊的水面泛着新鲜的泡沫,反射着白亮亮的天光,有些晃眼。站在田埂上抛秧是一件很快意的事,秧把子从一只只有力的手掌中甩出,带着秧叶相触的“簌簌”声,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青绿光滑的弧线,一发发榴弹炮炸响,“砰砰砰”溅起快乐的水花。秧把子不甚均匀地散布在水田里,由于重力的作用,一律的头朝上,卡腰立正的姿势,像迎候检阅的女兵,像等待摊开的墨团,又像一些期待敲响的音符。松开秧把子,插下第一棵秧苗,户农家的秧门便打开了。
最先被摁进泥里的是几排端直的“标秧”,就像我们单位上那些“标兵”或者“楷模”一样。绷了绳子栽种的秧苗,就象小学生搭着尺子写出来的字一般,焉有不齐整的?插秧和写字是一回事,被“标秧”隔出的一畦畦等距离的空间就像预先打在宣纸上的绿格子,那是书写的参照。和写字一样,插秧是要退着来的,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还要把握恰当的力度和方向。秧苗入土不能太深,否则“缓意”(秧苗苏醒,重新开始生长)太迟;更不能太浅,否则不安分的秧苗会浮出水面,还得补插。有人喜欢将秧苗斜插进水田里,就像写斜体字一样,一排排的秧苗整齐地倒向同一个方向,像美女刚刚梳理过的秀发。别担心,缓意过后,一棵棵秧苗都会挺直了腰板,一天天努力地试图接近太阳。插秧最讲究的是整齐端正、横竖有形,一棵棵秧苗插进泥里,应该像出操列队的士兵一样,个头等高,行列清晰,这样的行列有利于秧苗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加顺畅的呼吸。有那技艺超群的庄稼人,插秧时不用标竿比,也不用插了标秧提醒自己,依了笔直的田埂一路插下去,头也不用抬却能将那秧插得出奇地端正——插秧的高手完全当得起“书法家”的荣誉。农谚有云:“稀庄稼,吃饱饭。”说的是株距和行距的关系,过度的密植会因秧叶得不到足够的光合作用而减产甚至枯萎。这是插秧中最难掌握的关系,不好用数字加以精确,全凭年深日久积累起来的经验。此外,还得善于识别稗草,插秧的过程中随时将它们剔出扔掉。稗草的茎干颜色泛白且光滑,不似秧叶那样碧绿粗糙。仔细想来,熟能生巧,那经验和技艺,那距离和尺度,竟分毫不差的藏在农夫心里。
最感人的细节是将秧苗插进自己刚刚踩出的脚窝里,秧苗的生命里便注入了人的活动。那是不可避免的事,因为要退着插,经常就会将秧苗插进自己的脚窝里。脚窝有点深,不能绕过不插,也不能顺势将秧苗插进那更深的坑里,就只好伸出手从看不见底细的水里抠出些稀泥,将秧苗小心地埋进自己的脚窝里。秋天打谷子时候,在已然干涸的秧田里,你一定还会看见自己三个月前踩下的脚印,一些不曾插了秧苗的脚印竟异乎寻常地清晰,似乎还残留着插秧时脚板的温度。温暖亲切的脚印让你有了想亲近它们的冲动,于是你脱了鞋踩进去,竟分毫不差。一种历史感油然而生,多少年来,那片田地里,踩下又搅碎过多少个脚印,祖辈的,父辈的,你自己的,数也数不清。你被曾经的温暖和质朴、辛劳和收获激动不已!
最后一棵秧苗插下去的时候,秧门就关上了。收拾好农具,伸直了长时间佝偻的腰身,某块骨节“嘎巴”一声响,很酸疼!站在田头看自己的作品,视线穿越时空,从稀疏的点彩派的绿色图画里仿佛看见了金黄的沉甸甸的谷穗。这时你才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一般意义止的农活,插秧成了一件庄严肃穆同时又讲究点艺术修养的农活。往小里说插秧如写字,讲究的是端正整齐、疏密有致;从大的视角看,插秧如作画,讲究的是气韵生动、浓墨重彩。每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夫都是画家,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大地上描绘出世间最朴实最壮美的田园风光。年复一年,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播撒生命的绿色,才使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颓废荒芜。
我更愿意把插秧比作一首歌。白天,烈日当头,俯首插秧时,总有布谷鸟从头顶飞过,声声“布谷”仿佛催人勤奋,那是天籁般的协奏曲;晚止,皓月当空,新插的秧田里迎来了第一批歌手,为数不多的几只青蛙用“呱呱”声宣示着自己对这片领土不容侵犯的主权,那是交响乐队的合奏。秧苗成长的岁月里,始终有蛙鸣伴唱,那是大自然古老的歌谣。
有诗为证:“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这是宋人杨万里的《插秧歌》,是宋代田园诗的代表作。没有一般宋诗刻意讲究的深奥难懂的理,却也妙趣横生,读来亲切感人,它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古代农村插秧劳作的情景。
应是和睦幸福的一家人了,全家总动员,其乐融融地插秧。丈夫把秧苗抛给妻子,小儿子拔秧苗,大儿子插秧——有抛有接有拔有插,忙得不亦乐乎。孰料天公发威,大雨滂沱,雨中插秧又是兜鍪又是甲的,整个一场紧张的战斗。妻子招呼丈夫暂憩片刻且用早餐,可勤劳善良的丈夫照样低头弯腰劳作,转而嘱咐妻子要管好家里的小鹅小鸭,免得它们到田里糟蹋立足未稳的庄稼。真是时时尽力,事事操心,农家吃苦耐劳的品格,全部凝聚在这朴实的诗行里了。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农业机械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生产方式却自愿退回到千万年前的手工劳作,非得栉风沐雨、胼手胝足才得以完成一次又一次从种籽再到种籽的生命轮回。于是,古老质朴的歌谣又一遍遍回响于田间地头,回响在我们那渴望回归田园的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