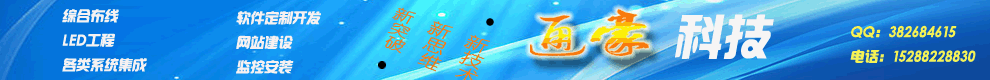一段难以启齿的双面人生
已经从事艺术工作的周锋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是不容亵渎的。不论当年还是现在,他们在临摹人体模特时,可以用“心如止水”来形容。一位雕塑家说:“我们4年的大学,有3年是上人体课,根本不会有什么想法,上课、学习、完成学分,或者说已经麻木了……”
而1996年的农村姑娘小莲,对人体模特这个行业完全是陌生的。在她看来,这是一个不能启齿的职业:羞耻、哭泣、拒绝,直到接受。
面前的小兰,40岁,看上去很憔悴,“压力很大,这几年,尤其是这几天打官司”,她禁不住哭起来。她是小莲的姐姐。1997年2月,她在妹妹的介绍下,从一名纺织女工转行为人体模特。
20年在昆明打拼,如今,小兰已人到中年,这些年,一家人一直租房子住,出租房就在麻园村附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对面她上班的云南艺术学院。“儿子问我在哪里上班,我就是指着对面的大学告诉他在那里面,儿子还小,他认为他妈在大学里面上班很骄傲。”
可是,儿子不知道小兰心里有多苦涩。她和所有孩子的母亲一样,早早起床,为儿子准备早点,送他去上学。然后再跟丈夫说自己要去学校扫地了。学校里8小时的课是安排满的,她要坚持坐8小时,按老师的指点摆出各种姿势,一天8小时,课上下来她可以获得100元的报酬。
中午和晚上,她都会和所有的家庭主妇一样下班回家到市场买菜,讨价还价,回家做饭,偶尔报怨一下因为工作的原因总是发作的腰疼病,叫儿子给她捶捶酸痛的背和腿。
这些年来,打工的丈夫并不知道她干的是人体模特这一行,因为还有妹妹和侄女和她一样在学校“扫地”,她隐瞒得很好,丈夫并没有任何疑虑。
“我告诉我姐,老师说我们是在为艺术献身。”小莲在兄妹中排行老九,小兰是老三。虽然自幼丧父,因为是家里的老小,在小莲的记忆中,她总是能感受到来自母亲、兄长、姐姐温暖贴心的照顾。
1996年的这次择业,让小莲为难了。
“是个好姑娘,身体条件好,敬业、单纯,好多学生都画过她。”“那个年代需要勇气,这是个有勇气的姑娘。”当年把小莲从人才市场领回来的周锋等7位同学至今都这样评价小莲。
第一堂课后,学生们都认为一定要想办法留下这个姑娘,否则,他们将再次面临不能上课的困境。7位同学开始轮流请小莲吃饭,为她打饭。学校的老师们也都来劝小莲留下来。
面对这些大学生和大学教授的恳求,小莲心软了。
可是,接受了这个职业,来自精神的重压让她喘不过气来。“上课就像行尸走肉,下课不敢出宿舍门,最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一向直言快语、活泼开朗的小莲,变成了另一个人:自闭、不敢抬头看人。3个月里她足不出校——孤单、无助、难过又漫长。她告诉当纺织工的姐姐她在给学校扫地没时间回去看她。
3个月里,小莲每天工作8个小时。那时候,做人体模特,一节课是4元钱,一天是16元钱,加上每个月学校发给小莲的150元的固定工资,小莲满足了。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半年后,一直跟三姐称自己在大学扫地的小莲决定跟三姐摊牌,因为学校老师叫她再帮助找几个人体模特。这个当初她认为要隐瞒家人一辈子的职业,她决定让姐姐也来做,“工资能保证生活,这是我们最起码的要求。”
刚刚失业的纺织女工小兰,就这样和妹妹一样,当上了人体模特。之后,是她们的侄女小芬。
她们的固定工资从最开始的每个月150元,1999年涨到了200元,2003年再涨到了每个月300元,一直到现在,固定工资仍是300元。
3个女人先后成家,但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干的这一行,这是她们彼此永远的约定。